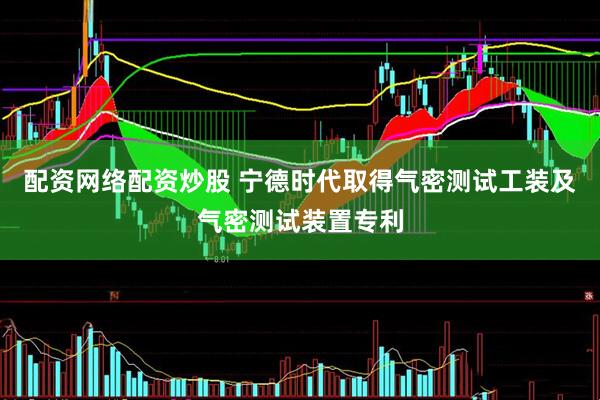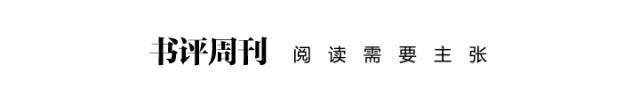 深圳配资开户
深圳配资开户
过了六月毕业季,七月往往是选择的十字路口。对于“明天”,我们眼下无论掌握多少知识和讯息,似乎都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判断。人类学者袁长庚称,这些年参加活动每到提问环节,他几乎都会被问到关于“面对明天”有什么建议。
这是一个并不容易回答的问题。甚至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偏巧这个问题又遇上了一个表面看上去更新、更炫目的时代,于是可能正在成为一个新的问题。在学者袁长庚看来,我们对“明天”有困惑,实际上是我们在当下迷失了,而当未来变得不确定的时候,“过去”也会变得难以言说。在今天的这篇文章中,袁长庚尝试围绕“明天”谈了些个人的思考,这些思考未必能够回应具体的困惑,但至少可以作为一种提示,提示我们犹豫不决时也可以想想——有没有假借看似真诚而迫切的对“明天”的追问,去回避直面当下所需要的勇气?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给明天的一句话》,篇幅原因有删减,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
 原文作者 | 袁长庚
原文作者 | 袁长庚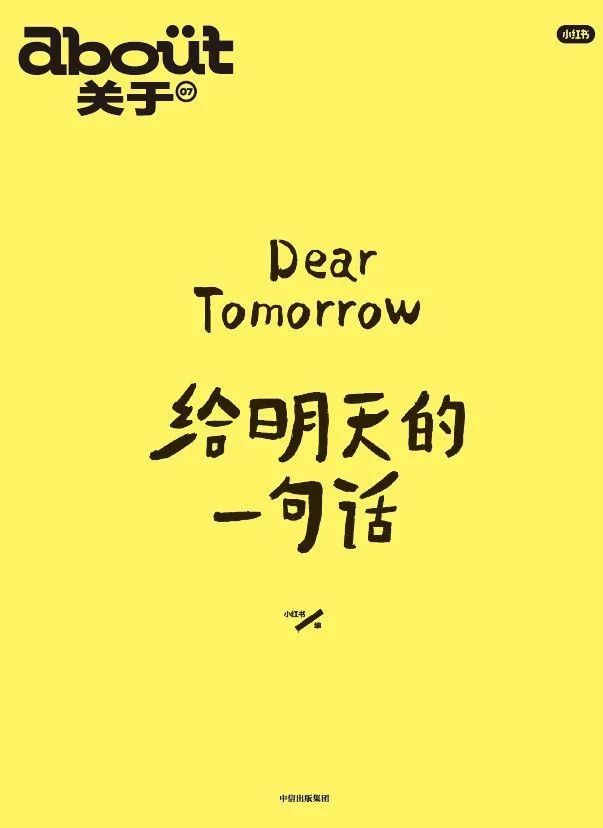
《给明天的一句话》
版本:小红书|中信出版社|24小时工作室
2025年5月
如何回答有关“明天”的问题
这些年来我常常参加一些与青年议题相关的座谈交流活动,无论活动具体的内容为何,到了观众提问环节,总有人让我谈谈有什么“面对明天”的建议。按照我的理解,讨论到了“未来”的层面,回答者应该有对人生或世界的彻悟,而我虽然人到中年,但距离这样的修行还差得很远。有时候左右推脱不过,只能就着当时的话头稍微说两句,事后想起自己的胡诌,难免懊悔。
曾经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屠刀下幸存的奥地利哲学家让·埃默里,在《变老的哲学》里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判断。他说在“年轻”时,我们常常可以把时间问题转化为空间问题。比如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想象未来,其实是在想象自己将在何处过什么样的生活。所以,我理解活动上年轻的朋友们追问我有关未来的建议,其实是想让我帮他们想象某一空间内具体的生活状态,而我的无能,恰恰在于只能给出一些笼统的规划和建议,无法勾画某种理想生活的样貌。有时候,说得越周全,越是难以面对别人赤诚的发问,甚至会显得有些油滑和虚伪。
因此,回答有关“明天”的问题,势必要让自己保有某种“年轻”的想象力,不甘于既定的轨道和秩序,不沉迷于对经验的墨守。想象未来,就是想象某种还没有被实践过的生活方案,甚至想象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有无新的可能。
有“哲学界猫王”之称的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2023年出版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Too Late to Awaken:What Lies Ahead When There Is No Future,中文可译为《现在觉醒已经晚了——如果没有未来,前路上等待我们的是什么?》。齐泽克的角度一向刁钻,在这本书里,他换了个方式谈论“明天”。比方说,我们已经在无可逆转的生态危机中越陷越深,注定会遭受灭顶之灾,那么在接下来这段走向终点的道路上,反思还有没有意义?
无独有偶,很多年前,英国著名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在《无所乐观的希望》当中也设定了一个类似的立场。伊格尔顿认为,正是因为曾经笼罩在我们头顶的各种“救赎”方案的破产,让我们能够好好谈谈什么是“希望”。在他看来,虚妄的乐观、“明天会更好”的陈词滥调都不是希望,希望应孕育于某种绝望——“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只能靠我们自己。”
《无所乐观的希望》,
作者:[英]特里·伊格尔顿
译者:钟远征
版本:新行思|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3年3月
两位哲人的思考,有助于我们换个方式重新提问,重新思考一下如何回答有关“明天”的问题。
工业革命将人类引入了一种崭新的生活状态,这种状态在学术上被称为现代性(modernity)。现代性有很多特征,其中之一是时间感的变化。简单说,现代人相信的是一种线性时间,“光阴似箭”,今天是昨天的明天。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就看破了这种关于“时间”的问题。工业社会的基本逻辑是生产——出售——获利,是1,000元的原料制成的产品卖出1,500元的价格。这种不断增值、不断发展的逻辑叠加在线性时间之上,就是“明天会更好”。我们无法让时钟停下来,“明天”总会到来,但是如果这个“明天”没有比今天更多、更好、更强,那么即使我们终将走入其中,也预示着一种失败。换言之,现代人给“明天”设定了一种衡量的标准,一个下滑的、停滞的“明天”是无意义的。
可以说,现代人之所以会对未来感到焦虑,其实是对某一种特定的未来感到焦虑:如果我辛辛苦苦上了大学但却过得还不如父母一代怎么办?如果我没有抓住当下的机会,错失了能够让自己变现、增值的风口怎么办?如果我现在选的这条路,未来并没有通向“更好”怎么办?作为现代人,我们不可能回头,回头就是退步。我们也不确定未来的方向,因为不确定当下的道路是不是能够抵达那个相对理想的未来。后退不得,前进又有些犹豫,进退维谷之下,“现代”也变得让人不安。
我们对“明天”有困惑,实际上是我们在当下迷失了,而当未来变得不确定的时候,“过去”也会变得难以言说。因而,一种总体性的无力感笼罩着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
假想一个注定失败的未来
虽然这是现代人的总体困境,但对于当下的年轻人而言,这又似乎是一个新问题。
中国是文明绵延数千年的大国,历史上我们的学问和智慧总是指向一个遥远过去的圣人时代,无论当下遭遇何种危机,似乎总有祖先的智慧可作荫蔽。清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先行一步的社会精英走出历史的温柔乡,转而想象了一个在未来的光明终点,抵御外侮、独立自强,从种种变法与革命到离我们更近的开放与改革,中国人始终都不曾动摇对未来的信心。这种驱动历史前进的巨大想象力,在新一代青年的身上渐渐有了冷却的趋势,他们的迟疑、犹豫、彷徨,跟“未来”的光和热渐渐衰减有关。这种大历史脉动的变化,表现在家庭层面,就是代际之间共识的破裂。子女一代认为父母辈的经验已经不再适用,两代人之间关于应该如何度过一生的设想完全不同,父母眼中的子女“身在福中不知福”,子女眼中的父母只是碰巧遇上了历史的红利期,“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对“未来”的困惑,以一种具体而棘手的状态浮现在生活的地平线上,这已经成为一个无可回避的挑战。
偏巧,这样的新问题又遇上了一个表面看上去更新、更炫目的时代。以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为代表的技术变革已经不再是小说和电影里的乌托邦,我们谁都不敢想象明天一觉醒来又有哪种颠覆性的技术即将“空降”到日常生活中。与以往技术变革的乐观不同,这一轮技术革新似乎隐隐带有“洗牌”的意味,不是大家携手进入明天,而是一种残酷的筛选机制,某些产业、某些群体似乎注定拿不到登上新方舟的船票。于是我们一边惊叹于技术的力量,一边焦虑于自己会否被变革淘汰。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里更是直接宣称,未来将有一些人沦为彻底的“无用阶级”。
于是乎,我们原本就难解的未来谜题,因为技术进步带来的“乱花渐欲迷人眼”而更加让人焦虑。我们越是惊叹技术的力量,就越是恐慌于被技术取代的可能;越是想要停下来读读书、静静心,思考一下自己的人生,越是被技术变革所掀起的前进氛围裹挟着,难以自处。便捷的信息终端把各种各样的声音强行推送到我们的手心,学术巨匠、行业精英有可能发出耸人听闻的警告,知识博主、流量红人却反而鼓励我们大胆进场,拥抱未来。比试卷上的难题更让人绝望的,是参考答案居然不止一套。
电视剧《人生切割术(第二季)》(2025)剧照。
事实上,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对网络上流传的各种对未来趋势的断言都感到怀疑甚至疲倦。与其说是因为我们有更全面的信息、更深刻的理解,毋宁说是生活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我们对那种被重复宣扬的线性时间想象感到厌倦。就像再高明的计算也不能100%预测明天早高峰时的天气状况一样,对于“明天”,我们眼下无论掌握多少知识和讯息,都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判断。如果执着于要问出个所以然来,就只能让自己陷入某种思辨的猫鼠游戏,要么近乎于盲信地“赌一把”,要么在种种顾此失彼当中耗尽心力。
于是,回过头看,我们或许更能明白齐泽克调转发问枪口的高明。齐泽克的策略是,通过假想一个注定失败的未来,给思考置入某种确定性。结局已定的“明天”不再值得我们猜度,这是对“明天”的某种解绑。一旦“明天”不再是问题,我们就只需思考“现在”。甚至进一步说,如果“现在”的一切都不会对“明天”产生效力上的影响,“现在”就成为一个姿态性、道德性的问题。
问题延展到这个层面,知识和利益的权衡反而不重要,重要的是信念。
“现在”才是“明天”的锚点
有朋友可能会说:放着信息、知识、技术不谈,非要把话题扯到“信念”这样的玄学字眼上,这不是胡扯吗?其实这不是齐泽克的发明。在人类历史上,很多文明恰恰是用这样的方式,应对看似无解的未来难题。
以我在人类学领域里相对熟悉的宗教为例——就目前的材料来看,无论是初民社会朴素的万物有灵信仰,还是文明成熟后发展出的制度化宗教,人类有力量的灵性生活,没有哪一种鼓励人们以“投资”和“风险规避”的态度面对未来。相反,它们总是希望你认定无常的必然、死亡的必然、毁灭的必然,然后反过来思考“此岸”的一生该如何度过。圣洁之爱的证言也往往强调我们的情感不因贫穷或富有、健康或疾病而有所增减,这就是用此刻去征服未来的不确定性。由此可见,无论是朝向彼岸的信仰,还是流连俗世的情感,在处理未来之问这方面的基本策略是相似的。
所以,在文明的视野中,“明天”不是某种前方的时间节点,而是一种能让我们返回当下的思考框架。如果人注定一死,如果世间繁华到头来都是一抔黄土,那么我们眼下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于是乎,“明天”成为一种召唤,但不是让你空想明天,而是让你找到安顿在当下的“法门”。无论前方等待的是审判还是轮回,当下的信念和态度才是关键。若信念有偏差,即便豪掷千金修桥铺路,或许也只是虚妄的执念,无济于最终的解脱。很多人都听过“泰坦尼克号”巨轮沉没之前,船上那只乐团不停奏乐直至被海水吞噬的故事。那些乐手未必都有笃定的信仰,可他们在面对无可逆转的结局时,选择用理念和态度标明自己的价值和尊严。
电视剧《人生切割术(第二季)》(2025)剧照。
在这种意义上,“给明天的一句话”如果是用以比拼当下谁更睿智、谁更通透,注定是一场输多赢少的赌局。这句话不应该是封印于时光胶囊中等待被验证的箴言,而是某种邀请,邀请我们以更为真诚的态度面对当下,对当下的生活有所交代。
命运这只九连环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如果你执迷于一定要参透“明天”,那么往往结局是首先牺牲“现在”;而为“现在”注入理念,往往也无心插柳一般地给“明天”找到了一个锚点。因此,我更愿意把“明天”当作一种思考问题的框架,这样的未来常常以否定的姿态出现:假如失败了呢?假如夭折了呢?假如期盼的事情没有发生呢?这样带有挑战意味的提问不是为了让我们陷入犬儒主义,相反,对抗空无的方式不是成为空无,而是面对空无依然有话可说。末日来临之前,我们依然可以爱他人、爱世间万物,依然可以关心粮食、蔬菜,依然可以阅读和思考——上述一切不能改变末日,但却能改变尚未被末日吞噬的我们。
与此相应,我所理解的给未来的一句话,其实是为当下留一份证言,不是为了最终可以被兑现,而是为了让我们在未来到来的时候,求得一个解释:我为什么这样度过了一生?因为我曾经选择过相信。
在那些被迫要回答年轻朋友们追问的活动现场,我常常给出这样的观点:正是在面对未来诸多不确定因素的时候,我们才应该认真地审视一下眼前的生活,问一下自己有没有因为某种盲目的执念,选择抵押此刻的爱和幸福,去交换未必降临的成功。或者说得更不客气一点儿:我们有没有假借看似真诚而迫切的对“明天”的追问,去回避直面当下所需要的勇气?
祝福所有的读者朋友都能因对当下的勇气和赤诚,获得坦然面对未来的可能。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刊发。作者:袁长庚;摘编:申璐;编辑:张婷。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2024书评周刊合订本上市!
点击书封可即刻下单深圳配资开户
线上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